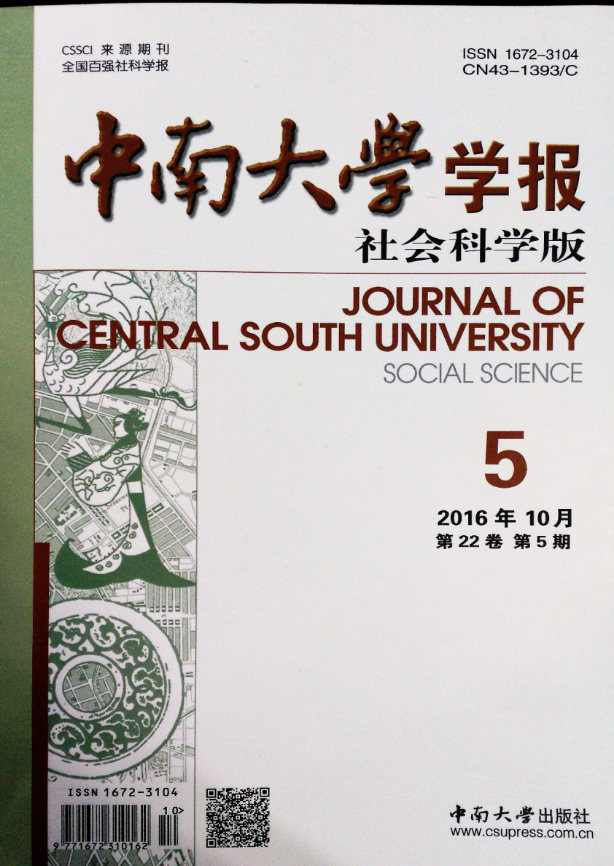欢迎来到西北政法大学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网站!
摘要:优良、健康的精神生活秩序在现代性社会中的生成,所遭遇和面向的是一个治理主体深刻转型与变迁所构建的复杂化精神格局。遵从精神生活治理主体的价值性本位及在当代社会中适宜性表达的正当性逻辑,彰显精神生活治理理性的公共性精神福祉,从人之精神性生存之价值本体境界处,重视与反思“人之精神生活生存权利共享与共生”的合理性存在方式及价值实践,就必须引入治理思维,从精神生活治理的维度引导中国社会走向人类精神生活公共性福祉的超越共享,探寻“精神生活治理逻辑的价值实践”,真正意义回应“精神生活自我治理”的本质及精神生活自我更新实现的价值路径。在精神生活治理理性生态化培育实践中,深植一种基于公共性、现代性精神特质的人之“本体性安全”的精神生活价值规范。
关键词:精神生活秩序;精神生活治理;公共性福祉;精神生活价值
中图分类号:B0-0
正文
“精神生活”危机问题在当代的突显,并非仅仅是一个偶然化、简单化的公共性精神文化事件,这不是一个西方工业文明的精神现代性模式的简单实践的结果,也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有的状况,而是一个兼具公共性社会转型和“复合现代性精神”逻辑运演的必然后果。精神生活治理问题的多层、多维度呈现真实地意味着:在我们这个“精神秩序”失调的大时代中精神生活本身成为一个问题,一个应值得我们每个人都认真对待的问题,精神生活危机的现象已经在社会生活各领域都可以看到,成为一个精神的梦魇和思维的缠绕。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精神生活困境问题,我们只有认真研究其内在发展机理及治理的法度,才能真正意义上发现精神生活的本体、结构特征、治理规律、发展逻辑。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入一个重要的挑战与机遇共存的历史性关节点之上。伴随改革中产生的中国阶层贫富分化所导致的中国人精神生活伦理秩序及正义结构的紊乱,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作为为一种公共性文明体的凝聚力。精神生活的“高调理想主义”和“低沉的犬儒主义”导致社会某种普遍公共性价值规范“意义与实践”消解,同时“主义话语的纷繁,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现实”。
一、精神生活失序、危机的实践理性剖析:
精神生活治理的回应型价值结构基础
当下的时代精神生活情景存在精神生活“生存安全性”危机、精神生活底蕴荒芜、精神生活结构碎片化断裂、精神生活高度复杂性困顿、精神生活无主体化迷茫、精神生活贫困、精神生活严重物化(以处理经济生活的方式治理精神生活)、精神生活价值选择的困难、精神生活公共性缺失、精神生活实践的扭曲化、精神生活重建的制度性阻滞等等“负化”实践状况,此种“负化”实践是一种“现时代精神生活的物化状况, 表现为精神生活舍弃自身的超越性, 甘愿附生并同一于贫乏而低俗的物化方式;从形式上获得感性多样性的精神生活, 受商品拜物教及其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的强势主导, 陷入了非理性的快感体验及享乐主义困境,人们的精神生活也由此呈现为种种病理状态。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使精神生活的物化处境进一步加剧。物化的本质仍然是异化, 反映了现时代在整个世界历史时代进程中的过渡性与不成熟性, 表明现时代的个体化与社会化尚未生成适于现代文明的精神生活样式”。[1]从精神实践本质上说,是因现代性观念布展与精神生活治理双重缺位导致,其主要困境主要表现为:实践困境即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而对精神生活治理的弱置;理论困境即“中国精神”观念创生远落后于改革逻辑实践;制度困境即断裂社会所构型的矛盾性效应及文化现代性危机等三个方面。
(一)精神生活治理弱置的集体行动逻辑:“德性与财富”内在逻辑紧张的社会实践
就“中华公共性文明体”内在性本质而言,支撑其质性的“公共精神生活”的观念形态的精神生活秩序出现危机与紊乱,则从机理的深层造就“中国精神生态”的失衡及公共性精神、公共性意识形态重建的困难。在全球现代性精神之再次冲击及压缩下中国精神生活的治理之高阶位必然低效和无奈地还原为“利益和权力的协调与平衡”。在人之精神生活的本原处集体性放置“德性与财富”紧张化的结构文化叙事,这可以说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87年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时期中国国家社会“精神生活”的基本语法。因为,就精神生活本身发展逻辑来看,这是一种常态与历史性必然的选择。在此种时代状况下社会成为一个可以分化的“物质集团”和“精神集团”的交互,精神生产力能够积聚起极大的创造力,推动精神劳动的发展,“精神劳动是自由劳动,是创造精神财富的劳动”[2]。创造精神财富的劳动其实是这一时期最迫切的文化叙事。但是,社会实践的现象层面的“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集体性精神实践表达出来的精神生产力建构了中国精神生活的基本维度。同时,集体性精神实践没有在“中国精神治理的整体性框架”完全发育成熟中就被迫走向了中国现代性的精神生活实践,民众无法选择、无法逃避。中国精神治理顶层设计及民众精神生活治理的缺失,根源于多元主体交互互动的精神生活治理主体生成的困境,即国家、社会、民众、组织等,对建构共同精神生活治理主体方面的参与度不高、公共理性生成机制不健全,导致现实改革的实践逻辑推进的受阻,其本质表现是“精神更替,革新的瘫痪”,精神生活治理被集体化的精神行动逻辑所掩盖,现实状况是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中具有巨大的力量,他们看着价格表不是为了寻求经济问题,而是在追求某种价值和精神无政府状态的文化创造。
(二)观念创生的逻辑桎梏:中国精神自我治理的观念围栏
照亮与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是人类实践本质力量生成的最终目的,照亮民众现代精神生活可以说是一切先进观念创生的根本旨趣。任何真正的哲学观念生成都是以自身特有的致思逻辑与理路,透显出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度反思、历史建构与批判性改造。处在深化改革的时代现场,尤其需要对支撑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国民“精神生活”运行状况进行哲学观念创生的思考、治理并建构适应时代发展的民众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治理成为一个鲜明表征我们国人“中国梦”践履时代的主题风格与内在质性价值诉求的范畴,是体现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应着力推进的“质性学术话语”。这不仅是一个人类恒久性的学术思考点,而且在普通民众的生活领域频繁出现的显性思考语式。可以说,对观念创生的逻辑桎梏超越及精神生活治理围栏的破除,就成为人类智慧比例和谐与优化的生存地基,成为我们时代一个突出的“精神地标”。然而,过去三十多年到现在,民众的精神生活健康性与经济增长性确实处于不匹配、不同步之中,民众在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建设中所享受到的愉悦与幸福感略显不足,在经济迅猛增长与精神生活优雅体验之二元张力中,社会实践结构的迅猛发展式突变与社会观念文化创新的滞后之间形成难以言说的“精神文化鸿沟”,因此,“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出现严重失衡,崇高精神追求淡化,部分人的精神荒漠化。面对社会的快速发展,有些人热衷于物质生活的提高,而忽视精神生活的发展。他们否认精神力量的重要性,鼓吹物质生活高于一切,把‘感官的享受’、‘物欲的满足’作为人生唯一目的”[3],“年轻的一代已经开始拒绝任何形式的社会普遍伦理,他们失去了对社会道德生活的基本信任。”[4],简单的说,此种精神文化鸿沟是物质生活发展后的现实精神生活状况与应有精神生活样态之间的距离。
(三)制度困境与文化现代性危机:社会实践结构突变的负效应
全球复杂性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实践结构的突变导致制度供给严重不足及文化实践出现秩序失衡,此种状况成为社会存在的一个基础性地平。“当代社会的重要特点是它表现的是生活的碎片,而不是一个连续的生活。当代社会充斥着复杂的‘现代性’幻象,使人们生活在失去自我、人格分裂、价值崩溃、理想失落和漂泊不定的梦幻般的生活中,人的生存境遇变得越来越糟糕。”[5] 碎片化的精神性存在,使人生存在被“复杂的物象化现实”包围之中,精神生活的实践自觉成为物性追求和制度理性的奴隶,这是一种深层的人性遮蔽化现实的出场。现代性文化价值被精神疾病折磨,我们整天面对并体验到的是现代生活画面的虚弱的线条、死板的色彩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喧闹的伪文化,个体显得烦躁不安,无暇深思,完全沉迷于自己的自我构境之中。每个生命个体都在现代社会的特殊人生体验方式中自觉地反映和接纳现代性复杂精神生活,外在世界的复杂性价值成为我们内心精神生活的真实图景,飞逝、碎片、复杂、矛盾成为个体内心最现实也最切身的文化现代性体验实践。每一个个别因素都陷入这种多样化的情景中。“事物从其孤立状态中解放出来”要么是通过追踪社会现象之间的真实关系而实现,要么是借助类比通过揭示可能关系而实现。精神生活世界中所有制度与文化现代性表达方式,相互之间都处于无法言说的多元关系中,没有一个能从其他事物相联系的大环境中剥离出来。从一个不安全的精神生活关系游移到另一不安全的精神生活关系,这种无着的相互追寻与纠结,始终无法理解公共性精神生活的安全性生存之所在,在无穷无尽的多样中迷失了自己,丧失了人格健全的公共性精神生活实践与文化现代性实践,更缺失了人之生存的本体性安全及人文制度理性。
二、精神生活治理的逻辑转型与基础导向:
精神生活公共性福祉超越市场逻辑
精神生活治理的场域就是市场逻辑,治理实践活动不可能在市场逻辑中自发生成,其必然要在人类精神公共性福祉的价值超越性导引下进行。在治理理性的自主价值逻辑中,市场逻辑为其不同治理主体的协调、互动提供了场所。但是,市场逻辑的负面效应同时也鲜明地突显出来,就是精神生活的物化及治理主体表达方式的市场化。在此,就必须建构一种适应市场逻辑,发挥市场逻辑中自愿互动、积极参与的正面效应,规避物化表达的消极性,真正体现人之精神性生存的实践本质化精神生活样态。以人类精神生活公共性福祉的超越性、价值先导性为核心观念,实现“价值信念先导与市场逻辑优先”的合理性实践共构。因此应该在市场逻辑与精神生活秩序构造之间选择一个合适的度,促进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在精神生活治理中保证市场逻辑中“利己性和利他性”的辩证统一。不断批判与发现市场化的精神生活文化中异化性与变异性现象,形成民众个体、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塑造精神性生存的治理基础,矫正和消除市场的利己性所造就的精神生活物化与变异文化载体的出现。因此,在市场逻辑正面效应与治理公共理性的双向导向上进行精神生活逻辑规制,就是真正摈弃单一精神生活集体化的治理或精神生活分类单一化治理,重新澄明、发现、发展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生活治理逻辑”,即在多元交往主体共在、共生基础之上的“总体实践化的精神生活公共性治理。全球复杂现代性背景下的当代中国社会,传统型的精神生活表达、实践秩序有必要主动与“现代社会”相匹配与统一。因此,从治理维度保障人的“精神生活尊严”成为精神生活治理逻辑的价值境界,以市场自觉性、积极互动性为精神生活治理导引点,在精神生活权利价值重构、机理反思的基础上,以治理公共理性的回应性、引导性、规范性、强制性等方式促使人的精神生活行为向人类精神生活公共性福祉转变,从而最大限度的构造优良精神生活秩序。
人类社会的精神治理逻辑实践一直以来指向着“人与世界”关系所进行的观念调整、价值发生,其具体形态与合理化的发展逻辑内在隐含的秩序就是人之“精神与灵魂”的现实矫正、优化。从精神治理逻辑实践的多变、多重关系格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精神生活治理逻辑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公共性价值呈现与发生。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则是“精神生活治理逻辑”进程中的转折性灵魂地标,正如伯曼所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力量和独创性,是怎样照亮现代精神生活的。”[6] 马克思真正把精神生活的治理逻辑从单向度的“多点式”导引到“总体实践化的精神治理公共性”生成与培育实践中,实现了人类精神公共性福祉超越市场逻辑,进而在现实生活世界实现了生存安全性维度之全新境界的“马克思精神生活治理逻辑”。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生产也是这样”[8]。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是鲜明的站在市场逻辑中认知精神生活的,市场逻辑中的物质生产和生活现实存在对精神生活的制约构成了马克思精神生活治理逻辑的基础与前提,这就为精神生活治理真正找到了存在与发展的现实地基与困境解决路径。马克思又说,“用改善各劳动阶级住房的办法就能有成效地减轻上述那些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用这种办法——仅仅用广泛改善住房条件的办法——就能把这些阶级的绝大部分人从他们那种常常几乎是非人生活的泥沼中,提升到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实实在在的高峰”[9],精神生活与精神福利的高峰就是对人之精神生活尊严的价值表达,马克思的精神生活治理的价值表达逻辑恰恰首先根植于“市场逻辑的物质生产与生活”改变中,马克思的精神生活治理价值逻辑启示就是,当代人用何种方式影响、改造市场逻辑中民众物质生产与生活是精神生活治理的根本性问题。此问题的破解马克思提供了两种方案,首先是“物质生产与生活”制度性、实践性改变,能够确立其民众精神生活尊严的基础存在形态。第二是,在此基础上,用先进、优良的公共性文化秩序造就一种整体性基于“生存安全性”的文化公共性社会关系总体,在其文化价值建构的社会场域中确立一种文化和精神存在的社会现实,改变世界的逻辑就是让不断生成的社会存在和文化价值现实照映精神生活领域中最核心的“精神生命的活力和精神福利”。这两种逻辑方式相互统一、不可或缺。同时,马克思也批判了一个无文化和社会存在之根的精神生活享有和治理方式,就是单向的改变民众的物质生产与生活状况,或单向提升民众精神生活。对此,马克思说,“于是,一个稻草人终于做成了,人们把它称作时代“精神”的体现者!”[10]
精神生活治理所关注的是社会之公共精神实践的共同体与人之为人的精神意义结构的实践合理性价值排序,以及多元主体协同互动之优化逻辑的公共理性的生成。精神生活治理的逻辑转型与基础导向就其哲学的本真意义而言,是对建立在“公共生活”“公共领域”及“国家与社会”场域之不同生存主体意义共生逻辑的正当性的公共性追求及规范伦理确立。精神生活治理是对精神生活领域突出的复杂性问题,通过国家、社会与个人,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以及全体民众等多主体参与合作,形成具有共生、共契意义的精神生活新秩序,进而有效性的遏止精神生活危机,重塑精神生活秩序、风貌,形成优良的精神生活发展逻辑。具体地讲,精神生活治理主要是从精神生活的“现象层面、发生学意义、形态结构、价值与生态秩序”等维度,通过国家、社会、个人多元主体参与及平衡实践共构,并实践合理性的界分不同精神生活治理主体的边界,在建立精神生活治理的文化价值与制度安全保障体系基础之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引,以“自发自治与协同共治”为机制,培育精神生活治理的公共理性,进而实现精神生活优化发展。力图在当代与永恒之间的重大关系问题中实现基于人类福祉的价值信念坚守与治理。
三、精神生活秩序重塑与革新:
精神生活治理逻辑价值实践境界
精神生活秩序重塑与革新是精神生活治理逻辑的价值实践境界的本质体现。精神生活失去自身生存尊严的直接表现就是精神生活秩序紊乱,原有的精神生活治理方式不能适应、不匹配新的实践结构范式。所以,精神生活秩序重塑与革新就是对真实精神生活治理实践的诉求,也代表了人类精神生活治理价值实践境界的提升。在库恩看来,危机是新理论凸显的适当的前奏,从一个处于危机的范式转变到新范式,远不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即远不是一个可以经由对旧范式的修改或扩展所能达到的过程。[11] 换句话说,当社会的民众的精神生活所处的困境已经成为一种精神性生存的瓶颈,就必须对旧的精神生活秩序进行重塑与革新。“当今时代被称为‘真实复兴’的时代。真实在当代的复兴,从本质上论述就是‘整体性’‘有机性’文化观念的复兴。”[12]而所谓“精神生活真实”则是精神生活自身生存秩序系统整体的、生态的、差异的、多元的、联动的表达方式,并同社会实践环境、机理、规律有机统一地运行,而且可以和外在客观世界形成良好的实践互动。精神生活危机、虚无、物化等病理的普遍性彰显是民众个体性的精神尊严缺失,其本质是文化整体性的社会关系总体性精神权利真实实践的受阻,精神生活自身无法自足性的表达与实践。精神生活治理的价值境界就是培育、生成“新型治理主体”,在精神生活自我治理机制运行中到达“精神生活真实”,具体说就是通过精神生活实践获得“‘自我的实在性’或心灵的真实性”。[13]
精神生活自治是一个在精神生活层面极为重要的概念,自治从一定层面说是对精神生活任意性的限制,是个体自我发觉生命品质的前提,并不是说没有精神生活治理人就没有正常的精神生活,而是正因为精神生活治理的出现才使得精神生活有了新的存在方式与形态,或曰重塑了“精神生活的新常态”,就像互联网时代一样,没有互联网人也能交流,有了互联网,人就在一个全新的维度中交流,业已和起初的交流维度有了质性的区分。人类各种实践活动都存在有“自治与共治”的治理维度。治理在其中使人类实践更加接近真实,同时在新的层面规定了精神生活的质态。这里所强调的精神生活自治不是指与既定秩序或共治的紧张关系,主要是指一种内在的、独立不依的精神立场,一种基于批判和自我批判形成。
在精神生活治理实践中,精神生活治理的价值结构、基础导向、价值境界、价值伦理正面临深层的变迁与转型,在精神生活自我治理和共同治理的“治理价值境界”实践中,精神生活治理逻辑的出场从历史与逻辑、主题与话语、内容与表达、规律生成等维度为精神生活走出危机找寻方法与路径。此种路径的实践表明:精神生活秩序的优化与重塑,只能存在于精神生活治理实践与人之精神性生存内在统一性中,而这一体系的关系不但构成人的精神尊严的权利形态,同时还从价值境界上推进着治理公共理性的生成。具体地讲,就是在整个社会和个体中构造一种“基于多元主体参与、交互、合作治理精神生活”的社会存在实践结构。因而,精神生活治理的时代价值境界与逻辑的核心就体现为精神生活的治理真实实践生成。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精神生活治理主体边界界定。现代社会构型的精神生活领域中,精神生活治理主体表现为多元、多层、多样的存在方式,主要有国家、社会、民众个体及社会组织等,从精神生活权利及尊严的价值理想处合理界定不同主体的边界,以精神生活治理新型主体培育为目的,通过国家、社会、个人多元主体参与及精神实践共构,生成精神生活治理新型主体,设计主体间相互信任的合作与幸福生活的价值规范,形成多元主体相互信任的精神生活机制。在此基础上,精神生活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互动,在互动中进行角色认定及边界划分。
二是精神生活治理伦理的逻辑构成及价值取向。精神生活尊严及权利的共享是精神生活治理伦理的核心灵魂,精神生活治理伦理就是对精神生活治理实践行为的正当性反思,精神生活自由秩序、精神生活文化制度、精神生活价值理念等构成精神生活治理伦理的主要方面。精神生活自由秩序体现着治理秩序的本质,治理行为的正当性就是通过精神生活自由秩序体现出来,精神生活治理伦理秩序是精神生活的良性与有效治理的内在要求。精神生活文化价值制度是治理价值理念的现实存在或外化,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必将一定的文化价值理念制度化为整套实践规制性制度,以此实现治理的公共理性合理培育。在治理公共理性生成中,必然是以精神生活价值理念为优先性的,因为精神生活价值理念前置性主导着治理理性,其存在的价值方式为精神生活治理伦理提供精神定向。
三是对精神生活治理内容的要素设定。精神生活治理就其所涉及的广度和范围而言,治理内容具体讲就是要确立起精神生活的治理场域、治理环境、治理伦理、治理结构、治理方案、治理目标、治理过程、治理方式、治理内容、治理对象、治理意义、治理评价。在这些治理内容设置中要考虑到精神生活治理内容与治理规模及负荷之间的关系,治理规模取决于治理内容,其产生的负荷将会对治理效应有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精神生活治理而言,“治理规模与治理内容”要有不同的分类化的划分与协同性的评估。
四是精神生活治理机制的实践运行。精神生活治理逻辑价值实践境界就体现在精神生活治理机制的运行实践之中,精神生活治理运行实践就是不断地平衡、优化地将社会精神文化习惯、制度安排和市场逻辑结合起来,为人之幸福、安全生存提供“舒适的精神生活公共性”,能够自动识别精神生活危机、确立方案化解冲动,并重塑精神生活新秩序,进而可持续性的增进精神福利,培育精神生活治理的公共理性,进而实现精神生活优化发展。
精神生活的治理逻辑是人之精神性生存的基础,并实质性从学理高度推进着人之多重生存层次与境界,在现实实践中,精神生活治理的出场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公共性、生存安全性的精神生活问题解决的方法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确立边界、协同确立方案治理,最终实现合作性地化解问题。这正是人类全球复杂现代性的展开逻辑,精神生活的治理逻辑正是力图在当代与永恒之间的重大关系问题中实现基于人类福祉的价值信念坚守与治理向度的开拓。
参考文献:
[1] 邹诗鹏.现时代精神生活的物化处境及其批判[J].中国社会科学.2007(5):54-63.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3.
[3] 陈春莲.健康精神生活研究——基于和谐社会的视野[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126-127.
[4] 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390.
[5] 袁祖社.公共性社会的实践——生存之境与合理价值体验的发生[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3):94-102.
[6] 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M].徐大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13.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4.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5.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96.
[11]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78-79.
[12] 袁祖社.公共性真实——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的基点[J].河北学刊,2008(4):12-17.
[13] 霍鲁日.静修主义人学[J].世界哲学,2010(2):92-100.
Responsive value paradigm construction and logical regulatory governance spiritual life
——Human well-being of the public nature of spiritual life beyond the market logic of human science knowledge
WANG Xuan
(Institute of Culture and Value Philosophy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Shaanxi 710063)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good and healthy spiritual life order in the modern society, which is confronted with the complex spiritual structure of the main body of the governan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o comply with the value of the main body of spiritual life management and the legitimacy logic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highlight the spiritual life governance rationality of public spirit, from the spirit of life, the value of the ontology, pay attention to and reflect on the "people's spiritual life and living rights sharing and symbiosis" rationality existence mode and value practice, we must introduce governance thinking, from the spiritual life management dimension to guide Chinese society to the public welfare of public welfare. And then explore the value of "spiritual life management logic", the real meaning of "spiritual life self governance", the essence of the spiritual life and the value of self renewal. In spiritual life management rational ecological cultivation practice, deeply rooted in a based on public modern ethos of "ontological security" spiritual life values and norms.
Key Words: spiritual life order; spiritual life governance; public welfare; spiritual life value
收稿日期:2015-06-19;修回日期:2015-11-07
基金项目:陕西师范大学2013年优秀博士论文资助项目“生存安全性”的人学逻辑——“美好中国”的价值实践( X2013YB08)
作者简介:王轩(1984− ),男,陕西周至人,哲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